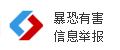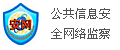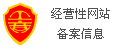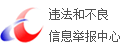|
题记:时间转眼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幸运的蜷缩在一个都市里生活了下来,虽然依旧忙碌却总算衣食无忧,每每拥着爱人总不能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是在深夜里自己总能被同样的恶梦惊醒,浑身上下冷汗直流,当终于确定自己是在做梦时,不禁长出一口气,悠悠的燃上一枝烟,看着红色烟头的一闪一灭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从前……… 七十年代末,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可能也是万般无奈与不情愿,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的降生并没有给家庭带来一丝喜悦,反而是更加的愁苦。虽然到现在许多地方仍然是重男轻女,但是到我们这里却有一点不同,这里的家庭更喜欢儿女成对,甚至认为女儿会更能孝顺和养老,儿子反而差许多;对于已经有三个哥哥的我来说,我的诞生只会加重这个家庭的负担。命运从一开始就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对一个迫切希望生一个姑娘的母亲来说失望和无奈是难免的,并且我的降生赶上了最早的计划生育,为此母亲日后笑称我是一袋小麦换来的。 几个月大的时候我的命运几乎发生了改变,如果不是最后母亲的依依不舍,说不定现在我会生长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也许会宠爱一身,当然这也仅仅是也许。尽管那些家庭非常想要一个男孩子,但是他们不可能从一个铁了心要把自己儿子抚养成人的母亲手中夺走,我是四个孩子当中唯一是母亲取的名字,她用自己学过的不多知识给我起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名字:春刚。 至今我还在疑惑,究竟是在我出生以后搬到村边的还是在我出生以前?这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我没有问过父母,只知道这个如今快三十年的房子早已经破败不堪了,西屋的房顶凹下去一大块,每次下雨总能蓄积许多的雨水,待雨停之后我和父亲还得上去用扫把一点点弄下去。老屋是典型的青砖土坯屋,里面的墙壁只是随便用泥巴抹了几下,窗户也是四方小木格子的,很小很小,屋子里的光线永远都是昏暗不堪的,里面每天都是尘土,屋角的被子上甚至会积下十几公分厚的土,这当中甚至会有从墙上剥落的大块的干泥巴。现在这个房子母亲仍然住在里面,如果不是从里面走出了两个大学生给它增加了些许不平凡,也许它的命运和其他老屋没有什么两样。而我的童年正是从它开始的。 从我懂事起,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饿,什么都想尝一口,家里炒菜从来就不会搁多少油,只是蜻蜓点水而已,这些油也是换来的最便宜的花油(棉花籽榨出来的,味道很难闻而且还有许多有害物质),但这已经是最好的东西了,家里吃不饱我就去地里找一切可以下肚的东西:秋天的蚂蚱(蝗虫)、紫色的野葡萄(一种直根系的一年生植物)、人家地里剩下的地瓜、野生的枸杞、有甜味的玉米桔杆等等还有许多我至今叫不上名字野生植物的茎快。春天地里几乎没有吃的,唯一剩下的零食也是添饱肚子的主食——馒头,就成了我们所有孩子的美味;可惜那会家里由于人口太多,孩子们都处于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加上产量有限小麦是绝对不够吃的,况且母亲还要用它来换取日常的生活用品及开销,平时都是玉米面窝窝即使是馒头都得加进去玉米面,我们家直到过年才能吃上真正的白面馒头。我的馒头永远都是黄色的只是黄的深浅不一样而已,我的小伙伴都是把馒头用菜刀切开中间撒上盐和少许香油,那时侯阵阵的香味直钻我的鼻孔我拼命吞咽着唾沫啃着自己的黄色馒头,有时候趁母亲不在家我和三哥偷偷的沾一点花油(不敢多了怕母亲会看出来)再加点盐,这样的美味我可不舍得马上吃光,我会用尽一切味觉嗅觉来欣赏,尽管它有着一股呛人的味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天下最可口的了。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得了脉管炎卧床不起,虽然他每天疼的哭爹喊娘,但是我知道父亲每天早上都要吃掉母亲亲手用开水冲的荷包蛋,我极少能吃到鸡蛋,所以我真希望床上躺的那个人是我而不是父亲,这样我就能天天吃到荷包蛋了。一天我去找人一起上学,我在他家看到他们在用油炸地瓜片,这在我们家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而且喝的是淋着香油的蛋花菠菜汤,一路上我看着他泛着油光的嘴,捂着自己被玉米面粥撑的发涨的肚皮暗暗的发誓:我长大了也要天天喝上菠菜汤,也能想吃就吃炸地瓜!
虽然我小的时候也特别盼望过年,但是年对于我来说却也有另外一种滋味。小伙伴们几乎每个人都是一身新衣服,但是我记得自己虽然也是新的但是却是母亲用别人剩下的布料给我做的花花绿绿的“百家衣”。由于我还处于贪玩的年纪每年过年后不久我的裤子屁股上就是两个洞,许多年我都记得穿的是补丁的衣服,里面是哥哥们剩下的秋衣裤,破袜子母亲修修补补我再接着穿。鞭炮是不会有多少的,不过每年表哥都会给我几挂鞭炮,我和三哥舍不得把它们一次都放了我们把它一个个拆下来,慢慢的放看着被我们炸的飞多高的塑料瓶子,满心的欢乐都写在了脸上。姑姑那会和奶奶一块过年,奶奶把所有的积攒都拿出来我清楚的记得那会奶奶每年都炸一种虾片,而我也只能吃几块就被奶奶收起来了,但是姑姑家的大表姐却可以随便吃,有一次我想吃她几块拌白糖的西红柿被她粗暴的拒绝了而且还把我给训哭了奶奶就站在旁边却并没有制止的意思,那个中午我是哭着回到自己家吃的饭。虽然只能在奶奶那里分到一点坏了的苹果梨什么的但是对于美食极度匮乏的我来说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我没事就去奶奶那里希望能给我一点哪怕剩下的也行。这里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外婆,虽然那会她的生活也不怎么样,但是她老人家把仅有的零食都给了我,从冰糖到饼干,从水果到蔬菜只要外婆能有的几乎都给我弄过来,这还不包括她给我“偷”表哥的小人书(连环画)。有时候得知外婆要来蹲在家门口等我的外婆是我一天当中最大的期盼。 跟头把式的熬到上学,我们一堆小伙伴都扛个小凳子背一个家里的花书包(很大也很破的),每天我们稀里糊涂的上学又稀里糊涂的下学,没有课本在一年级,每天老师发一根粉笔让我们在“课桌”(用水泥和沙子垒成的一块板下面垫几块烂砖头正面很平整适合粉笔写字)上学习写字或者算术什么的,然后老师基本一天就消失了,期末就放假几乎没有人管。我们就这样天天如此。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活动我的童年将会是一片黯淡和凄惨。 如果不是童年中一年四季的丰富多彩多少冲淡了一些痛苦的回忆,那么剩下的就会是无边的痛楚。春天里先是央求哥哥给糊风筝然后和小伙伴一起放看谁的飞的更高,或者攀援到杨树柳树上折嫩枝拧掉皮做笛子吹抑或傍晚逮满树的金龟子(我们叫老包)。夏天逮知了蝉什么的烤着吃,或者在下雨的傍晚寻找蝉的幼虫放到蚊帐上面看它第二天变化成蝉,由于它要变黑所以蚊帐上面不免沾上很多的黑点所以大人往往会狠狠训斥一顿,我极大的爱好就是在夏末去舅舅家地的附近逮蝈蝈(家乡叫优子,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就对一件事情拥有极大的耐心,蝈蝈很难逮到单单是发现它们的存在就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它们拥有巨大的牙齿稍不留意会狠狠的咬你一口,所以在逮的时候必须胆大心细,每次我都逮的最多,回家的路上我还要分给它们几个。 我最爱的是秋天,大地到处金黄,拥有可以果腹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单单是烤玉米炸蚂蚱就足够让我口水直流,所以每次我都会早早准备好捕蚂蚱的工具(一根结实的短竹竿头部捆一个圆形铁圈,铁圈周围是一个用纱布围起来的兜子),等一放假(农村那会还实行麦假和秋假)就迅速的扑到地里的怀抱,只需半天我的收获就会满满一小塑料袋,在秋天里我往往会长几斤肉而我们家的猫也会发福;秋收的尾声最香的食物是闷地瓜,地瓜被刨走以后总有一些遗留在地里,这时需要你耐心的寻找,比它更需要耐心的活是垒砌一个土坷垃窑,我知道这是能否最后吃到喷香扑鼻的闷地瓜的关键,一般步骤就是下面挖一个圆形的坑用稍大一点的坷垃做底层并留一个烧火口,上面是稍小一点的造型是个圆的慢慢往里紧就像最后合拢的石孔桥一样,中间的任何一个步骤稍不留意就会前功尽弃,最后是找来的柴火,深秋的大地里到处都是可以燃烧的秸秆,我们一般找一些耐烧的秸秆,慢慢的烧土坷垃窑,待烧到一口唾沫啐到上面顷刻间蒸发完毕后就算烧差不多了,把多余的炉灰掏出去,先砸烂一些土坷垃在下面赶紧把准备好的地瓜放进去再把剩下的土坷垃全砸进去用铁锨拍平夯实,上面再盖上一层土剩下的工作就是耐心的等待了,一般过一天过去扒开上面的一层土时浓浓的烤地瓜香气就会勃然涌出,这样闷出来的地瓜粘软香气经久不散尤其是烤糊的那块周围更是美不胜收。
冬天我既爱又恨的冬天,爱它因为到那时候已经基本上没有农活了父母也不再天天逼迫你下地给牛割草或者是别的什么事了,所有的星期天你都可以在外疯跑而不必担心回家会受到责骂,这时你可以天天尽情的玩三角(纸折叠的三角纸片,游戏规则为将对方三角打翻即为获胜),玻璃球,自制的陀螺,自制的风车,自制的打火柴的手枪(用铁丝做个手柄上面是自行车链条一节一节拼合而成,最前面的两节是用自行车轮上的称条冒磨细后用锤子慢慢砸进去,枪栓一般是用钢条前段稍微磨细后后面拴上皮筋即可)在晚上到处打火柴枪,由于到处是玉米秸秆所以那会村子里经常失火,现在想想和我们关系还是很大。但是那会大地里再也没有可以尽情果腹的东西了,即使是网到几只麻雀也是瘦小枯干出于怜悯我都会把它们放走,零星的美食就是火炉边上的几块吃剩下的馍馍片,在火炉旁烤一个昼夜后就会发黄变得香脆,这样的馍馍片实在是太少因为几乎就不可能会剩下多少馍馍可供烤着吃的,要不就是在地理寻几块剩下的甜菜疙瘩回家央求大人切切用锅加水熬制,待到最后锅里会沾上一层黏黏的深棕色的糖稀,这时我会迫不及待的拿筷子沾上,那根软软的细线会越拉越长直到没入你的嘴中,虽然有点发苦虽然有点牙碜但在贫瘠的冬季里这已经是顶级的美味了,当别的孩子都在期盼下雪时我却无比的害怕雪的到来,我没有一双可以防湿的靴子,棉鞋也只有一双破的,下雪后我只能找一些破塑料布绑在鞋上腿上希望它能保护我唯一的棉鞋,但往往事与愿违,回家后靴子已经很湿了并冻的瑟瑟发抖,我怕母亲会因此责怪常常等到天黑再回家。 快过年了,所有的小伙伴都是喜气洋洋,他们比我拥有多得多可以高兴的事情,我每次都是孤独的躲在田野里,漫无目的的游走,甚至是西边的大坑,我拿着从家偷来的火柴恣意的到处纵火点燃枯黄的野草,看着火苗吞噬荒草我总有一种报复的惬意;晚上我仍然游走在田野看着偶尔燃放的烟花,我知道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甚至会一路狂奔一路恣情的狂啸,我那时也不知道自己小小的年纪究竟有多少不能与外人道的苦楚要发泄,直到跑累了喊累了才一头栽倒在麦地里无声的抽泣,为自己不能言说的童年!
|


 主页 > 汽车 >
主页 > 汽车 >